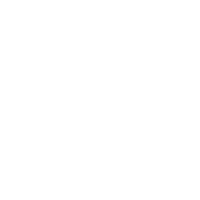民间故事: 十两恩情债
发布日期:2025-12-14 14:15 点击次数:110

山阴县有个孤儿名叫仇六,父母在他五岁那年染上疫疠双双死亡,留住他一个东说念主在这世上孤单无依。亲戚们王人嫌他是个株连,谁也不愿收容,小小的仇六便运转了流浪乞讨的生计。
那年冬天相称冷,雪花像鹅毛般飘了三天三夜。七岁的仇六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,脚上是用草绳绑着的破芒鞋,仍是两天没要到一口吃的了。他缩在县城东街的屋檐下,小脸冻得青紫,嘴唇裂开一齐说念血口子。
“喂!小叫花子,这是老子的地皮,滚一边去!”
一个十五六岁的叫花子狠狠踢了仇六一脚。这东说念主混名“癞头三”,是这一带叫花子的小头目。仇六痛得瑟索起来,却不敢哭出声——前日他因哭出声又被癞头三打了一顿,脸上的淤青还没消。
“三爷,这小子怀里好像有东西!”另一个叫花子眼尖,伸手就往仇六怀里掏。
“莫得……真的莫得……”仇六死死护着胸口,那是早上一位好心大娘给他的半个窝头,他舍不得吃,想留着来日再吃。
“拿来吧你!”癞头三一把扯开仇六的手,抢过那半个仍是冻硬的窝头,“嘿,还藏食!兄弟们,履历履历他!”
几个叫花子围上来拳打脚踢,仇六只能抱头瑟索。等他们打够了远抬高飞,仇六才逐步爬起来,抹掉嘴角的血,一瘸一拐地离开这里。肚子饿得油煎火燎,目下一阵阵发黑。他知说念再不吃东西,只怕真要饿死了。
走过香满楼酒楼时,仇六闻到内部飘出的饭菜香气,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下来。他绕着酒楼走了一圈,发现后墙有个被野狗刨出的豁口,刚好能容一个孩子钻进去。夷犹再三,求生的盼望礼服了战抖,他四下查察,见无东说念主选藏,便瘦小的身子一缩钻了进去。
落地后,仇六失望地发现这里不是厨房,而是酒楼的后院。院子很大,长满半东说念主高的荒草,墙角堆着些破酒坛烂木桶,看方式仍是放置许久。正想退出去,忽然听到一阵“哼哧哼哧”的声息。循声望去,院子最里头竟有个破旧的猪圈。
仇六蹒跚着走往日,只见圈里趴着两端憨态可居的猪,正懒洋洋地晒着冬日难得的阳光。见到生分东说念主,两端猪仅仅抬了抬眼皮,又延续打盹。
“唉……”仇六看着这两端猪,心里涌起一阵酸楚,“我还不如你们呢,至少你们有吃有住,不会挨打。”
倡导落在猪槽里,仇六的眼睛猛地亮了。那猪槽里竟是酒楼来宾吃剩的残羹剩饭——天然仍是馊了,但里头有白米饭、碎肉渣、菜叶子,以致还有半块竣工的馒头!这些东西在仇六眼里,简直比八珍玉食还要诱东说念主。
他再也顾不得许多,翻身跳进猪圈。两端猪吓了一跳,“哼哧哼哧”退到墙边,深嗜地看着这个不招自来。仇六扑到猪槽前,用手抓起那些残渣就往嘴里塞。冷掉的饭菜带着馊味,可饿极了的仇六那里顾得上这些?他大口大口地吞咽着,眼泪却无声无息流了下来——我方怎样就活成了这样?
吃饱后,仇六打了个响嗝,看着那两端惊疑不定的猪,竟生出几分歉意:“猪兄,对不住了,抢了你们的食。”
他爬出猪圈,刚走几步,就听一声大喝:“哪来的小贼!”
一个酒楼伴计拎着猪食桶站在院门口,看到仇六,立即高声呼喊:“抓贼啊!有小偷!”
几个凶神恶煞的伴计冲进来,圮绝分说等于一顿毒打。棍棒如雨点般落下,仇六只以为周身骨头王人要断了,临了目下一黑,什么王人不知说念了。
等他醒来时,发现我方被扔在城外的乱坟岗,周身高下没一处不疼。他招架着想爬起来,却使不上力气,只好躺在那里等死。也许是命不该绝,那天傍晚,一个拾荒的老夫途经,见他还有气,喂了他几涎水,又留住半个饼子。靠着这点水和食品,仇六硬是撑了过来,拖着伤疤累累的体魄,又运转了流浪。
转瞬又是几年往日,仇六十二岁了。这年冬天来得相称早,刚入冬就下了场大雪。仇六还穿着那件破棉袄——如今仍是短得遮不罢手腕,补丁也磨破了,表露黑乌乌的棉絮。芒鞋早就穿烂了,他用破布裹着脚,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他仍是一天整夜没吃东西了,又冷又饿,目下阵阵发黑。走到孟家庄村口时,终于援救不住,“扑通”一声倒在一户东说念主家门前。
这家的主东说念主姓孟,村里东说念主王人叫他孟老头。老头本年六十有二,膝下无儿无女,老伴三年前病逝,如今只剩他孤零零一东说念主过日子。好在有条黄狗与他作念伴,这狗名叫大黑,是孟老头从小养大的,通东说念主性得很,孟老头走到哪它跟到哪。
孟老头的日子过得贫苦,但总不忘分一口吃的给大黑。大黑也通东说念主性,从不嫌家贫,白昼随着老头下地,晚上守门看家,成了老东说念主独一的慰藉。
这天早晨,孟老头早早起来扫雪。推开院门,就见门槛外蜷着个黑乌乌的东西,走近一看,竟是个半大孩子,表情青紫,呼吸微弱。老头一惊,连忙放下扫帚,冗忙地将孩子抱进屋里,放在炕上,盖上家里最厚的那床被子。
“大黑,去灶膛边守着,我把火生旺些。”老头说着,往灶里添了几把柴。大黑听话地趴在灶旁,眼睛却盯着炕上的孩子。
孟老头煮了碗姜汤,一勺勺喂进孩子嘴里。好一会儿,孩子眼皮动了动,缓缓睁开眼。
“孩子,你醒了?”孟老头松了语气,“你是哪家的?怎样倒在雪地里?”
孩子招架着想坐起来,却周身无力。孟老头扶着他,又喂了几口姜汤。缓过气后,孩子“扑通”跪在炕上,朝着孟老头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。
“老爷爷,谢谢您救了我……我叫仇六,是个孤儿,仍是一天没吃东西了……”
看着孩子瘦得脱相的小脸,孟老头心里一酸:“你躺着别动,爷爷给你作念碗热汤面。”
孟老头来到灶间,舀出小半碗宝贵的白面——那是他留着过年包饺子用的。和面、擀面、切面条,作为虽慢却沉稳。面快下锅时,老头忽然以为腹中一阵绞痛,怕是昨夜着了凉,连忙放下手中的活,急急往后院茅房跑去。
出恭纪念,老头洗了手,延续煮面。面煮好后,他拿落发里独一的鸡蛋,在碗边磕破,打进去。看着黄白分明的蛋花在面汤里翻腾,老头咽了口唾沫——他仍是泰半年没尝过鸡蛋了。
盛面时,老头忽然发现碗里掉进了一小团灶灰。他连忙用筷子去挑,可那灰烬散开了。看着这碗难得的好面,老头简直舍不得倒掉。他夷犹顷刻间,伸手从碗里握起沾了灰的那块鸡蛋,放进我方嘴里吃了,然后才颤巍巍地把面端到屋里。
此时的仇六早就饿坏了,看到那碗热热闹闹、香气扑鼻的面,眼睛王人直了。他接过碗,也顾不得烫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面里竟然有鸡蛋!仇六仍是记不清前次吃鸡蛋是什么技艺了。他吃得又快又急,烫得直咧嘴也停不下来,转倏得一大碗面就见了底,连汤王人喝得一滴不剩。
孟老头在一旁看着,眼睛湿润了。等仇六吃完,他才轻声问:“孩子,你多大了?爹娘呢?”
仇六抹了抹嘴,把我方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说到这些年受的苦,孩子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孟老头搂着他羸弱的肩膀,泪如泉涌:“苦命的孩子啊……”
仇六在孟老头家住了下来。说是住,其实也仅仅有个遮风挡雨的场地,吃的依然是稀粥咸菜。但仇六很得志——至少无用挨打,无用挨饿,晚上寝息有屋顶,还有热炕。
住了七八天,孟老头把仇六叫到跟前,摸着他的头说:“孩子,你随着爷爷,也只能遭罪。爷爷老了,没次第,你年事还小,不如出去闯闯。”
说着,孟老头颤巍巍地走到炕柜前,从最底层摸出个破布包。那布包裹了一层又一层,足足裹了七八层,才表露内部的东西——是几块碎银子,加起来概况十两。
“这是爷爷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。”孟老头把银子塞到仇六手里,“你拿着,去镇上或者城里,找个活计。你这样贤惠,去大户东说念主家当个书僮,或者去酒楼当个伴计,总能混口饭吃。”
仇六捧着银子,手王人在抖。十两银子!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多钱!他“扑通”跪倒在地,朝着孟老头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,额上王人磕红了。
“孟爷爷,您的大恩大德,仇六这辈子王人不会忘!我一定好好干,等挣了钱,一定纪念孝顺您!”
孟老头扶起他,笑得满脸皱纹王人舒伸开:“好孩子,你有这份心,爷爷就得志了。只消你能过上好日子,爷爷比什么王人忻悦。”
第二天一早,仇六背着孟老头给他准备的干粮和几件旧衣服,揣着那十两银子,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孟家庄。孟老头和大黑站在村口,一直望到他的身影消散在小径至极。
日子一天天往日,转瞬等于十年。
孟老头更老了,背驼得锐利,步辇儿要拄手杖。大黑也老了,毛色失去了光芒,步辇儿慢吞吞的。这些年,老东说念主过得愈加贫苦,但总会在吃饭时,对着空座位说一句:“六儿如若纪念,该有多好。”
村里东说念主王人知说念孟老头在等谁。阿谁他当年救下的小叫花子,一走等于十年,音尘全无。有东说念主劝他别等了,说那孩子怕是早就忘了这穷场地。孟老头仅仅摇头:“六儿不是那样的孩子。”
这年秋天,孟家庄忽然吵杂起来。村里东说念主奔跑相告:仇六纪念了!不是阿谁瘦小同情的叫花子,而是个有钱的大老爷!坐着马车,带着仆从,穿着绫罗绸缎!
消息传到孟老头耳朵里时,老东说念主正在院子里喂鸡。他手里的簸箕“咣当”掉在地上,鸡食撒了一地。
“真的?六儿……六儿真的纪念了?”老东说念主声息王人在发抖。
报信的邻居欢快地说:“金科玉律!就在村东头老祠堂那儿,正在给仇家眷东说念主分钱分东西呢!孟老伯,您当年救了他,他笃定第一个来看您!”
孟老头激昂平直脚王人不知该往哪儿放。他忙回屋翻箱倒箧,找出那件唯有过年才穿的半新褂子换上,又把头发梳了又梳。想了想,他把家里独逐个只下蛋的母鸡杀了,炖在锅里。鸡肉的香气飘出来,大黑馋得直打转,孟老头拍拍它的头:“大黑乖,等六儿来了,我们一块儿吃。”
他从晌午比及太阳偏西,又从薄暮比及月上中天。桌上的菜热了又凉,凉了又热,仇六恒久没来。临了,老东说念主叹语气,盛了碗白米饭,就着咸菜吃了。他把鸡肉预防肠收进碗柜,对大黑说:“六儿今天笃定是太忙了,我们来日再等他。”
第二天,孟老头又等了一天。薄暮时,他简直等不住了,盛出一半鸡肉,端着去了邻居徐禄家。
徐禄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,心肠热,这些年没少照料孟老头。见老东说念主端来鸡肉,徐禄很骇怪:“孟老伯,您这是?”
“徐家兄弟,这鸡你收着。”孟老头强打精神,“我吃不了这样多。”
徐禄看出老东说念主表情永别,再三追问,孟老头才朦拢其辞地说,仇六纪念了,却没来看他。
“什么?”徐禄眉头一皱,“这不可能!您是他的救命恩东说念主,他岂肯不来?”
正说着,徐禄媳妇从外面纪念,一进门就欢快地说:“住持的,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?仇六!哎呀,那悦目,那派头,真确切饮水念念源了!我听东说念主说,他在城里开了家大酒楼,买卖好得很!”
徐禄看了孟老头一眼,预防翼翼地问:“那……他去看孟老伯了吗?”
媳妇一愣:“这倒没神话……不外,他给仇家每户王人送了五两银子和一匹布,应该会去吧?”
孟老头低着头,缄默回身回了家。那一晚,他坐在炕上,望着跳跃的油灯,整夜未眠。
第三天上昼,孟老头正在院子里晒玉米,忽听门外一阵喧哗。昂首一看,只见一群东说念主蜂拥着一个穿着高贵的须眉朝这边走来。那须眉三十明年,白白胖胖,穿着绸缎长衫,腰间挂着玉佩,手里还把玩着两个玉核桃。
孟老头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,才认出那等于仇六——天然胖了好多,但眉眼间还能看出当年的影子。
“六儿!”老东说念主激昂得手杖王人丢了,蹒跚着迎上去,“真的是你!你纪念了!”
仇六在离老东说念主三步远的场地站定,高下端详了一下孟老头破旧的院子和一稔,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他使了个眼色,死后一个膀大腰圆的仆东说念主向前,将一包银子“啪”地放在院中的石磨上。
“孟老头。”仇六启齿了,声息冷淡,“这是十五两银子。十两是当年你借我的,五两是利息。我们两清了。”
孟老头呆住了,脸上的笑貌少许点僵住。他望望银子,又望望仇六,嘴唇哆嗦着,却发不出声息。
这时,徐禄听到动静赶过来,正看到这一幕。他火气“噌”地就上来了,大步向前指着仇六:“仇六!你这是什么意念念?孟老伯当年救你人命,收容你,把棺材本王人给了你,你就这样答复他?”
仇六表情一千里:“徐禄,这里没你的事。当年的事,我自有筹划。”
“你有什么筹划?”徐禄怒说念,“要不是孟老伯,你早就冻死饿死在雪地里了!”
仇六冷笑一声,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十年的话:“是,他是救了我,给了我一口吃的。可你们知说念吗?那天他给我作念面,半途出去出恭,纪念连手王人没洗就延续作念面!这还不算,盛面的技艺,他竟然把手伸进碗里,握起一块鸡蛋我方吃了!我其时饿得快死了,硬着头皮吃下那碗面,心里却跟吃了苍蝇相通恶心!一个叫花子亦然有尊荣的!”
一番话如好天轰隆,孟老头蹒跚一步,简直跌倒。徐禄赶快扶住他,老东说念主表情苍白,周身发抖,半晌,才颤巍巍地说:
“那天……你饿得王人快没气了……我急着给你作念吃的,出恭纪念是洗了手的……碗里掉进了灶灰,我怕你吃了生病,又舍不得扔掉那鸡蛋,才我方吃了那块沾灰的……你……你怎样能这样想……”
老东说念主说着说着,泪如泉涌。十年的期盼,等来的竟是这样一番诛心之言。
徐禄气得周身发抖,指着仇六骂说念:“仇六啊仇六,我看你是银子挣多了,良心却被狗吃了!孟老伯我方舍不得吃鸡蛋,王人留给你,你倒嫌他脏?我告诉你,东西脏了可以洗,东说念主腹黑了,可就洗不干净了!你等于个负义忘恩的虎豹!”
仇六表情乌青,冷哼一声,回身就走。仆从们蜂拥着他远抬高飞,留住孟老头瘫坐在院子里,像个木头东说念主。
从那天起,孟老头就病倒了。徐禄请了医师来看,说是急火攻心,加上年事大了,怕是难好了。老东说念主躺在炕上,通常望着房梁怔住,嘴里喃喃着:“怎样会这样……怎样会……”
大黑似乎知说念主东说念主病了,整天趴在炕边,寸步不离。夜里孟老头咳得锐利,大黑就急得呜呜叫,用头蹭老东说念主的手。
这天夜深,孟老头陡然病重,呼吸穷苦。大黑急得团团转,忽然冲出房子,跑到徐禄家门前,拚命用爪子刨门,又高声吠叫。
徐禄被吵醒,开门见是大黑,愣了一下。大黑冲他狂叫几声,回身往孟家跑,跑几步又回头看他。徐禄心知不好,连忙跟往日。
等徐禄赶到时,孟老头仍是唯有出的气莫得进的气了。见徐禄来,老东说念主招架着收拢他的手,断断续续地说:
“徐家兄弟……我……我不成了……这房子,还有村东那两亩地……蓝本……蓝本是想留给六儿的……当今……当今给你了……你是个好东说念主……”
说着,羞辱的泪水从老东说念主眼角滑落,“我……我等于想不解白……当年那孩子……明明很懂事的啊……”
话音未落,老东说念主手一松,永久闭上了眼睛。
徐禄这个七尺汉子,抱着老东说念主尚多余温的体魄,号啕大哭。大黑趴在炕边,发出悲凄的哭泣,像是在哭,又像是在呼叫主东说念主。
徐禄厚葬了孟老头,就在村后的小山坡上,那里能望见进村的路。埋葬那天,村里来了好多东说念主,王人是受过老东说念主恩惠或照料的。唯独仇家没东说念主来——仇六前一天就带着仆从回城了。
办完凶事,徐禄想把大黑带回家养着。可大黑不愿走,白昼暮夜王人趴在孟老头坟前,不吃不喝。第三天早上,徐禄去上坟,发现大黑仍是死了,体魄蜷在坟边,头朝着坟头,像是睡着了。
徐禄的眼泪又下来了。他把大黑葬在孟老头坟旁,立了块小木牌,上头刻着“义犬大黑之墓”。
说来也怪,自从安葬了孟老头和大黑,徐禄的日子逐步好起来。那两亩地异常深奥,庄稼年年丰充。他又用孟老头留住的房子开了个小杂货铺,买卖竟也可以。村里东说念主王人说,这是好东说念主有好报。
三年后的春天,山阴县传来一个消息:仇六死了。
据说是在外县收账纪念的路上,际遇了流落。他和仆从王人被杀了,财帛被攫取一空。等官府发当前,尸体仍是被野狗啃得只剩尸骸,凭着衣服和随身物件才认出来。
仇家东说念主去收尸时,哭得天昏地暗。可村里东说念主擅自王人说,这是报应。当年他那样对待救命恩东说念主,如今落得尸骨无存,亦然老天有眼。
徐禄神话后,千里默了很久。第二天,他买了香烛纸钱,来到孟老头坟前。计帐了坟头的杂草,摆上供品,烧了纸钱。又在大黑坟前放了一碗肉。
“孟老伯,大黑,仇六的事,你们王人知说念了吧。”徐禄斟了三杯酒,一杯洒在孟老头坟前,一杯洒在大黑坟前,我方端起临了一杯,“王人说佐饔得尝,天理循环。可我以为,您当年救他,也不是为了图什么报应。您等于心善,看不得孩子遭罪。”
他叹了语气:“只能惜,那孩子最终没显豁,这世上比钱更紧迫的,是良心。”
风吹过坟头的柏树,哗哗作响,像是在恢复他的话。徐禄又站了一会儿,才逐步下山。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一直蔓延到山下阿谁泄气的小村落。
而孟老头和大黑的坟,永久静静立在山坡上,守着这片他们生计过的土地,守着那些对于温顺与感德、反水与救赎的故事,一年又一年。


“苦差使”酿成豪迈活!50岁犬子让父母的茶果坐上了“专属飞机


把好药品“安全关”滨州市市集监管局潜入开展药品假想和使用尺度


两市ETF融券余额环比增多2.12亿元


暖锅底料、菜品不取得收再使用!川渝结合制定圭臬


民间故事: 十两恩情债


首批科创创业东谈主工智能ETF持续上市